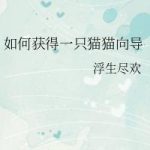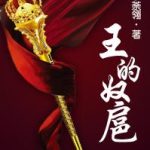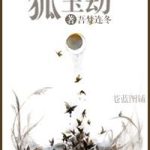進程十
喪事後,一切如常,随之朝堂多了一個話題“後繼儲君孰為”。
陛下倚坐在龍椅上,聽着衆臣的争辯。
“陛下,臣以為應立彭正王為儲君。”
“陛下,臣駁議,儲君應立嫡立長,敦素太子乃陛下嫡長子,兩者均占,更無皇子能及。太孫殿下乃敦素太子嫡長子,臣以為應立太孫殿下即位儲君。”
“陛下,太孫年幼,難以承擔重任,臣請立彭正王。”
“陛下,您已立太孫,應順位承繼。”
……..
陛下已經不耐煩了,連連止住。“行,行,行,一大早上争來争去沒意思,你們都沒主意,還向朕進言,再細細思量吧,退朝。”
待衆臣紛紛散去,“齊國公,高将軍,來正殿。”
兩位被單獨請到了正殿。
陛下詢問道,“兩位對立儲之事有何想法。”
“陛下,臣認為應立彭正王。”高将軍道。
“呵呵。”陛下笑了,“你這舅舅這麽不袒護外甥,換了別人巴不得自己外甥做皇帝。”
“臣不敢,太孫過于年幼,不能承擔重任,況且臣戍守邊關,難以參政。”高将軍解釋道。
陛下表情微妙,打趣道,“跟你爹真像,就喜歡在那個北鎮呆着。”轉頭又問齊國公,“你怎麽看。”
“陛下,應立彭正王。彭正王宅心仁厚,但行徑不失果斷,是為儲君之選,況且子嗣興旺,有福佑大徽百年之象。”
“額,福佑大徽,這可是你說的。”
陛下坐到幾案前,“你們回去吧,朕再做思量,如今朝中形勢不穩,兩位多加提防,以免有人生出非分之心。”
自安葬敦素太子後,太子妃便一直昏睡着,好不容易醒來,又不肯吃什麽東西。
“姑姑,姑姑。”挽意伏在床前輕喚道。“你倒是吃些啊,這樣耗下去是不行的。”挽意沒有叫起,回頭看向東宮女官,只見她搖了搖頭,連她都沒勸動。
“唉,姑姑,不好好吃飯就會有壞人把你抓走了,快起來吃些吧。”挽意想辦法哄着太子妃吃飯。沒有勸動。
“姑姑,我想吃您包的包子了,您再給阿意包一次吧。”還是沒有勸動。
沒有辦法,挽意又伏到太子妃身旁,“姑姑,過幾日父親就又要回北鎮了,再見他又不知何時了,他定是想你的,你要是這般樣子,讓他怎得放心啊。”太子妃側過身看着挽意,“你父親那,我,我好久沒見他了,讓他來見我。”
太子妃起了身,吃了些東西,這可把東宮女官高興的。
這世間,只有親情能找回人的心。
太子妃顯得有些虛弱,面頰蠟黃,強撐着坐了起來。挽意在一旁侍候着,看着太子妃這個樣子也是不由得心疼。前一刻還有些虛弱無力,看到高将軍進來立馬打起精神,嘴角努力的上揚。
高将軍依着禮給太子妃作揖。
太子妃招呼着讓他坐到自己身旁,又讓所有人都出去了。
“令俞,快讓長姐看看,你怎樣了,是胖了還是瘦了。”太子妃說話有些費力。
高将軍俯下身來,笑道:“長姐好好看,令俞很好。”兩人四目相對,高将軍看着太子妃布滿血絲的雙眼,“您操勞了。”格外心疼,又不知如何。
太子妃撫着高将軍的臉,搖搖頭,“只不過是有心無力罷了。我早想過會有這麽一天,又不敢面對,等到真正降臨時,又傷心過了頭。我真傻啊,人都不在了,我還這般做什麽。”
高将軍見慣了刀光劍影,血濺沙場,生離死別,如今卻不忍心再聽下去,深深的垂下頭。
兩人怔了好久,高将軍坐了下來,說起了正事。
“立儲之事,朝廷怎樣決斷。”太子妃問。
“朝廷分立了兩方,一方請立彭正王,另一方請立太孫,各方均有争理,不好說。不知您何意。”
“太子臨終前,讓我同嚴讓讓位東宮。”
高将軍有些震驚,“這,這是敦素太子之意?”
太子妃點點頭。
“那如此,可請示陛下做出決斷,立彭正王為繼太子。您同太孫退而避之,此為良策啊。”
“我也想如此,如今嚴兒已經不再是孩童,朝中衆人說他年幼,但他已有自己的想法,只怕他不會屈服。若是這般,豈不是置他于不顧,到時朝廷動蕩,便一發不可收拾。”太子妃憂心道。“按規矩他要在儲陵守上幾日,立儲之事等不得,由不得問他了。”
太子妃緊緊抓住高将軍的手,“令俞,今日便上書請立彭正王,沒有太子在這東宮我有些喘不過氣來。”說着竟哭起來,“你帶我回家吧,我要出去。”
太子妃有些神志不清,“娘娘,娘娘。”高将軍厲聲叫道,她瘋魔般的向外走,“不,不,我是你長姐,不是什麽娘娘。帶我回家….”一個踉跄,癱坐在地。
她仰起頭,聲音裏帶有微微顫抖,“令俞,長姐護不住你了。”
頓時,高将軍的淚水滾滾而下,“連連答應,好,好,我聽長姐的。”又把太子妃父親來安歇,離開了東宮。
去正殿的路上,內臣侍女紛紛向他行禮,步伐有些踉跄,紅着眼,環視着四周的城牆,他不知道,也不敢想這些年太子妃是如何熬過來的,自責當年自己的魯莽,不管不顧去了北鎮,深深的自責。
正殿裏,陛下遣散衆人,獨自參閱着什麽。只見上面字體清秀,端正大氣,陛下細細端詳每一章字跡,用手臨摹着每一個字,寫着寫着淚水打濕了字跡,陛下小聲抽泣,一遍遍地拍打着幾案,像在抱怨什麽命運不公。陛下一把推開,癱坐在龍椅上。
那字跡的左下方寫着“伯钺”。
“伯钺”是敦素太子的小字…..
第二日朝會,仍論立儲之事。
“陛下,臣等請立太孫殿下即位東宮。”不知何時,主張擁立太子一方的勢力崛起。
陛下向下撇了一眼高将軍,只見他搖搖頭,見他也不知此番狀況。“高将軍,你說。”
“陛下,昨日臣與敦素太子妃商議,她願與太孫讓位東宮。”
朝堂一片嘩然,尤其是擁立太孫一方。“高将軍,你怎麽…”
于公于私,高将軍擁立彭正王并無利。
此時東宮,太子妃獨自到書房取走了太子留給他們母子的奏表。
“太子妃到——”朝堂再次掀起一片嘩然。
但無人阻攔,都怔怔地望着太子妃走到了陛下面前。
太子妃跪倒在地,“妾代敦素太子奏表,敦素太子留表妾與太孫讓位東宮。”雙手呈上。
陛下也是吃驚,小心地打開奏表翻閱着,手不停的顫抖着,問道:“這是敦素太子之意。讓你們母子讓位東宮?”
“回陛下,天地可鑒,敦素太子病重時,特托妾将來将此表呈于陛下,以表東宮忠孝之心。”太子妃一字一句,叩首臨地。
陛下仔細翻閱了數次,“衆卿,既然敦素太子遺願讓位東宮,那朕便由不得衆卿争辯了。”
陛下思慮半晌,“傳召,立彭正王為繼太子,太孫改立安郡王,尊敦素太子妃為安郡王太妃。供奉不易,宜享尊榮。”
“臣等遵旨。”
衆臣散去,高将軍攙扶着安太妃離開了大殿,“您為何這麽做啊。”高将軍問道。
安太妃笑道,“是時候做個了結了。若我不出面,還不知此事要移到何時啊,萬一陛下何日遭遇不測,到時就不止這麽簡單了。”
陛下将自己的潛邸賜作了安郡王府,讓他們母子居于京中。
安郡王适才從儲陵回來,得知自己被封為安郡王,由不得他反應,便搬離了東宮。住在郡王府的第一晚,安太妃問他:“嚴兒,你可不滿。”
郡王的回答讓人有些意外,“母親,這樣也好,遠離那些紛紛擾擾,只有我們母子兩個,兒子求之不得,若是朝中有需要的,兒子也會盡力幫的。”
安太妃笑道,“過幾日你舅舅便會北鎮,你在朝中無人幫扶,你有幫得上什麽大忙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安分守己的好。”
一連數日,忙于朝事,好不容易父女兩才有機會坐下來好好說話。
“父親,快嘗嘗,都是姑姑交我的。”挽意向高将軍展示着自己的廚藝。高将軍嘗了一口,只見眉頭緊鎖,不由咀嚼便吞咽下去。
糟了鹽放多了。
又故作鎮定,“好,挺好吃的,我家阿意進步了。”
挽意也知道,父親在騙他。連忙端了出去,“父親,深夜吃了不好克化,我給您留着,明早再吃。”
挽意依偎在父親懷裏,他懷裏真暖。
高将軍溫柔問道,“阿意怎麽不同先前一般叫爹爹了,你一直叫着父親,我有些不習慣。”
“女兒長大了,不再是之前在父親懷裏撒嬌的小姑娘了,怎能還同先前一樣。”
“也是,我家阿意長大了,對了,你多大了?”
挽意一臉詫異,“父親怎麽這般記性,阿意今年及笄了。姑姑還特意給我做了一件百蝶衣,可好看了。”
高将軍喃喃道,“這麽久了,你娘被貶走七年了,我在北鎮也待了七年了。”
高将軍回想着,七年啊,彈指一揮間,仿佛一切還發生在昨日,雙親還在,妻子還在。可如今只剩下他一人了。
“父親,父親。”挽意打斷了将軍,“你在想我母親,我也想,這些年京中的貴女門都笑話我沒娘,說我沒規矩,可每次都是姑姑替我出面,可如今…”
高将軍鄭重的告訴女兒,“阿意,如今不同了,你姑姑再也護不住你了,你只能靠你自己了。”
其實挽意都懂,她姑姑從太子妃成了安太妃,從朝廷前退到了幕後。今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了。
大徽帝錄,志:元慶二十二年,敦素太子薨逝,世宗皇帝封太孫為安郡王,居于定京。
敦素太子留下的那道奏表,陛下私藏了起來,将東宮正門雍德門改為思雍門。
自改立太子那日起,他每日都去坤福宮,自己一個人對着敬德皇後的牌位說話,跟她念叨着他們的長子,伯钺長的,伯钺短的,總覺得一直說不盡,也沒人知道到底說了什麽。
直到第二年的初春,陛下臨晚時,去了坤福宮宿在哪了。直到第二日一早,到了上朝的日子,陛下不曾起身。
陳公公去喚,“陛下,陛下,該上朝了。”
陛下還是躺着,一動不動,“陛下,陛下。”
陳公公湊近些,貼近陛下手時,只感到一陣涼氣。他先是一陣惶恐,手不由得顫抖着,“陛下,陛下。”
陛下已沒有氣息了,僅一夜,在昨日夜裏他走了。
這位皇帝毫無征兆的崩逝了。
“咚,咚,咚,咚….” 山陵崩!
他懷裏抱着長子留下的奏表,和敬德皇後的牌位,離開了。沒有給次子留下一句話就離開了。
或許是對發妻的思念,對長子的愧疚,靜靜的走了。
大徽年代錄:志,元慶二十三年,世宗皇帝崩逝,谥號章順。